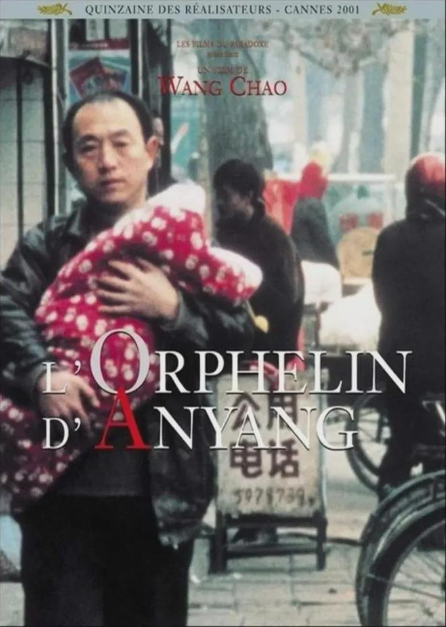我就只敢评论,人家觉得我好像评论得还挺好的,“哗”地一下就把我围了起来,我觉得那会儿想要成为领袖也挺容易的,只要你说的话有见地,大家就会对你表示认可,文学的民主性就体现在它是平等的。
我这个人就喜欢较真,我觉得如果你文学的东西都不敢较真,其他地方你就更不敢较真了。所以说我的这样一种劲儿,这种脾气,其实都是在南京这个地方养成的。
于兄你是什么时候到南京?
上下滑动观看王导详细发言
于奎潮(主持人):
我是1983年来南京的。
王超:
那么我有一个问题,你作为一个外地青年,你到了南京这个文学之都,你是怎么切入这座城市的?
于奎潮(主持人):
我很愿意接受王导作为嘉宾对主持人的提问。
但是我还是要说,刚刚王导非常巧妙地、有选择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他说自己从事电影创作的动力之源,是来自文学的涵养,我非常认同。我认为文学是我们从事所有文化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一个营养基。
我们读中文系的人,如果分析一下大家毕业以后的去向,其实做什么行业的都有……甚至也有去做律师的,还有做程序员的。但是最多的出路还是从事文化工作,写作或者从事教育工作。
在我们具备了一定的文学素养之后,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可能都会有一个意识,那就是创造的意识。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创造的意识就是创新的意识,尤其是从事过文学写作的人,做任何事情都会力求与众不同,所以我觉得这点是文学带来的一个很明显的好处。

《孔秀》剧照
为什么王超导演一直在讨论文学,以及八十年代的文学氛围?因为这与他的电影《孔秀》息息相关。这部电影的主人公孔秀是一个工厂的女工,她经历了两段非常不顺利的、甚至可以说是悲惨的婚姻生活,她最后终于从婚姻中出走了,出走了之后,生活还得继续,是什么支撑了她的精神?
看过电影的读者朋友们会了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所涌起的文学热拯救了她。就像刚刚几位老师讲的那样,在那个年代,文学真的是风起云涌,那个时候每个角落都有文学的身影。
王超:
咱们还是少谈点《孔秀》吧。刚才听了曹恺老师对“新浪潮”这个词的讲述,我觉得南京有几个文学创作者就很符合“新浪潮”的气质,除了曹恺老师,还有朱文。我觉得韩东有点像侯麦,他有那种睿智的感觉;朱文像戈达尔;包括后来的曹寇,像特吕弗。我觉得都挺像法国电影的“新浪潮”气质。
我看了大量的电影以及电影理论,这促使我更接近当代的文化的先锋性。而传统的文学理论在我看来有点滞后了,哪怕是当代文学理论,也更无法跟上当代文学和电影的实践,因为这样的实践是没有传统的,它并不因循守旧,电影永远尊重现实和当下,永远尊重你看见的。
我感觉今天在场的嘉宾都气质鲜明,中国文学里面难得出一批人说气质鲜明,如果把朱文和韩东放在一块儿,一冷一热的对比多么强烈,真的是这样的。
曹恺:
刚刚讲到了法国的“新浪潮运动”,当时其实对中国整个电影圈的影响都很大,因为大家看到那些新浪潮影片,其实都很晚了,都是已经到DVD碟片大量面市以后的了,在那之前,我们很多时候都只能读到一个故事梗概。
我有个朋友当时读了《去年在马里安巴》这部小说,他先读完了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原作,读完书以后他没有办法紧接着就看到电影,然后他就想象着,依靠他自己脑补,想象了一部电影。等到他真的看到阿伦·雷乃拍摄的《去年在马里安巴》这部电影的时候,他说:“拍得不行,没有我想的好。”

《去年在马里安巴》电影海报
我们要允许他这么讲(笑),我觉得我讲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当时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观看环境中来对待电影和文学之间的这种不同。电影语言和文学语言之间的相互补充,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王超:
史铁生就非常喜欢《去年在马里安巴》,他可以一段段背诵。
三、“向八十年代致敬”
曹恺:
我2000年的时候在半坡村做电影放映,然后有一次就是在放映《去年在马里安巴》,到最后放到了深夜一点半,全场只剩下四个观众,电影放完了以后都准备散了,当时有一个观众提出要求:“我刚刚看的不过瘾,能不能再放一遍?”然后当时办公室老板还是郭海平,他都快昏倒了,只好又放了一遍,这一遍结束就到天亮了。
那个时候确实大家对电影的语言有一种非常饥渴的渴望,有时候越看不到,越是想看。其实《去年在马里安巴》的剧本就是要触发人想象的。